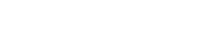第524章公主和亲
玉王一大通话说完之后,原以为会气得暴跳如雷的文宣帝,反倒是一脸平静的睁开了昏花的老眼,半会吐出一句话来,“朕因
何生气?”
玉王气结,把老头子嫡亲的公主外嫁去了桑国给一个老头子做妃子,这做父亲的不是应该气得跳起来吗,怎么到了他这里,反
倒是一脸的太平相?
这不科学啊!
尚不知其实文宣帝内心里已经翻江倒海,这个和亲政策,许多年前,前朝羽汉王朝之时,公主那就得叫下嫁,是为了和诸多小
国以及封疆大吏搞好关系,到得他们现在这里,就只能叫和亲了。
并且是,这样对稳固大楚国江山极有益处的政策,他为什么要气得暴跳如雷?
女儿们嘛,别以为他不知道,勋贵们的嫡女们出嫁是为了两姓之好,为的增进交流,还要搭上好几个庶出的姑娘,如果不是没
有好几个公主,他甚至想要建议玉王再多搭几个庶出的公主陪嫁。
只是,同时了解儿子比了解自己更多的文宣帝也知道,这个傻儿子想不出这种开创性的政策,指定是他手下哪个家臣提出来的
。
瞧他这一脸的傻逼相,似乎是瞅准了自己会生气的傻样,这还真是不够了解他这个做老子的啊!
如今的文宣帝后背发凉,同时更感觉,他自己也好,自己这个傻儿子也罢,似乎都落入了一张看不见的网中,无论怎么挣扎都
无法挣脱。
更或者是在说,他们都是执棋人棋盘中的棋子,不管你愿意不愿意,总有一股力量推动着你做这或是做那,可这结局倒也说不
上不够好,这就更让他感觉不妙了。
任凭感觉再如何不妙,文宣帝都没办法想出这所有的幕后之人,以及幕后之人的真正目的。
比如说国玺失踪之事,孙公公不知,一直掌管着国玺的太监亦是不知,他堂堂的皇帝其实哪里又知道呢?
有时候他真想自暴自弃的将玉玺交出去,可是,他想说的是,国玺在玉王逼宫的前几天时间就已经莫名失踪了,这话可有人肯
相信?
当时他发现之后,那个在值时掌管国玺的官员就已经失踪了,为防意外,当时他自己也没敢声张,只是让暗卫营私底下查探此
事,就连身边的孙公公他都没告诉。
只是,暗卫营的实际首领偏偏是大理寺的游冰,游冰在玉王逼宫前几天,出皇城时就已经失踪了,这让苦逼的文宣帝连寻个替
自己做证的人都不可得。
就如同那个依旧被关在地下水牢中的慧智大师一样,文宣帝同样是连求死或是做主动禅位的资格都无有,只能这么求生不得求
死不能的躺在床上做个活死人。
文宣帝搞不明白,梅园中的韶华同样有点蒙圈。
因为两相有意,又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,桑国与大楚国之间的共开互市,互利互惠,并且还要远嫁秀缘公主的决策以前所未有
的速度,在腊月中旬就已经拟下了双方协议。
之所以未签订正式协议,那还不是因为,大楚国那枚成了精的国玺一直没有下落吗?
不过这事儿同样没拦住合同的正式签订,因为玉王身边现在是人才济济,比如红叶谷的大方道长一听这件事的前因后果,当时
就乐了,“殿下,这根本不是问题啊!”
玉玺都没找到,正式的国书签订不了,这还不是问题,那什么还能称之为问题?
生着一嘴络腮胡须的大方道长呵呵一乐,“殿下,大楚国开国以来,可有签订过此种国书?”
玉王一怔,下意识的回道,“却是无有呢!”
“那不就结了,既然无前例可循,咱这就是头一份啊。
既然没啥具体规定的头一份,谁说了算?
咱自己说了算啊,再者说了,国玺是用在大楚国的国家大事上的,没谁规定外事合约是必须要盖国玺的吧!”
玉王一琢磨也乐了,对啊,他这是形成了固有的思维定式,以前但凡有国家大事,都要盖一份国玺,一来显得郑重,二来感觉
承载着国运的国玺能够起到足够的压制作用。
习惯成自然,不仅是他,连着满朝文武都如此,一听说要答定国书,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国玺。
“道长高议啊!”红叶谷出品,当是不凡,这名声还真不是吹起来的,“惭愧惭愧!”大方道长似模象样的拱了拱手,“食君之禄忠
君之事,当是也。”
这话玉王爱听,吃着我的用着我的花着我的银子,听我差遣,这个没毛病。
“依道长之意,当如何行事?”玉王最近一段时间,因为诸事不合,处处需要仰仗着这帮心腹,也颇有了些礼贤下士的模样,起
码表面现象如此。
大方道长仔细想了一下,这毕竟是代表一个国家尊严的外事印玺,断不可草率,不仅不能草率,而且还不能有可仿性,起码那
些个胡萝卜是仿不来的。
不过,所有这一切,都难不住素有心机的大方道长,于他来说,这都不是事儿,是故慨然道,“殿下,不如找几位臣工前来,大
家一起先商议一下外事玉玺的印刻模式和处理方法,然后再寻人篆刻如何?”
虽然大方道长做这种事得心应手,可他前世虽然没有得到过叶梨歌那般系统的皇储的教育,耳濡目染间,也知道凡事不能急于
求成,更不能一力揽功从而招人忌恨。
有好处大家一起拿,你好我好大家好,这也是帝王平衡术的一种。
玉王当即就差小太监去请人了,这事儿宜早不宜晚,赶想出办法来,赶紧把秀缘公主打发到桑国去。
就说这是个好办法嘛,前段时间,原本狄人已经有大兵压境之势,可韶家人在桑国边境和大楚国边境传出了,桑国要与大楚国
结盟,并将文宣帝之嫡女秀缘公主嫁与桑国老国王和亲的消息,狄人立马就收兵了,一直到如今,不明就理的狄人也没敢冒然
来犯。
这不就是个好兆头吗?
玉王的智囊心腹们没多少时间就齐聚御书房,听得玉王几句简要的说明之后,齐齐伸出大拇指,“妙啊!”
何生气?”
玉王气结,把老头子嫡亲的公主外嫁去了桑国给一个老头子做妃子,这做父亲的不是应该气得跳起来吗,怎么到了他这里,反
倒是一脸的太平相?
这不科学啊!
尚不知其实文宣帝内心里已经翻江倒海,这个和亲政策,许多年前,前朝羽汉王朝之时,公主那就得叫下嫁,是为了和诸多小
国以及封疆大吏搞好关系,到得他们现在这里,就只能叫和亲了。
并且是,这样对稳固大楚国江山极有益处的政策,他为什么要气得暴跳如雷?
女儿们嘛,别以为他不知道,勋贵们的嫡女们出嫁是为了两姓之好,为的增进交流,还要搭上好几个庶出的姑娘,如果不是没
有好几个公主,他甚至想要建议玉王再多搭几个庶出的公主陪嫁。
只是,同时了解儿子比了解自己更多的文宣帝也知道,这个傻儿子想不出这种开创性的政策,指定是他手下哪个家臣提出来的
。
瞧他这一脸的傻逼相,似乎是瞅准了自己会生气的傻样,这还真是不够了解他这个做老子的啊!
如今的文宣帝后背发凉,同时更感觉,他自己也好,自己这个傻儿子也罢,似乎都落入了一张看不见的网中,无论怎么挣扎都
无法挣脱。
更或者是在说,他们都是执棋人棋盘中的棋子,不管你愿意不愿意,总有一股力量推动着你做这或是做那,可这结局倒也说不
上不够好,这就更让他感觉不妙了。
任凭感觉再如何不妙,文宣帝都没办法想出这所有的幕后之人,以及幕后之人的真正目的。
比如说国玺失踪之事,孙公公不知,一直掌管着国玺的太监亦是不知,他堂堂的皇帝其实哪里又知道呢?
有时候他真想自暴自弃的将玉玺交出去,可是,他想说的是,国玺在玉王逼宫的前几天时间就已经莫名失踪了,这话可有人肯
相信?
当时他发现之后,那个在值时掌管国玺的官员就已经失踪了,为防意外,当时他自己也没敢声张,只是让暗卫营私底下查探此
事,就连身边的孙公公他都没告诉。
只是,暗卫营的实际首领偏偏是大理寺的游冰,游冰在玉王逼宫前几天,出皇城时就已经失踪了,这让苦逼的文宣帝连寻个替
自己做证的人都不可得。
就如同那个依旧被关在地下水牢中的慧智大师一样,文宣帝同样是连求死或是做主动禅位的资格都无有,只能这么求生不得求
死不能的躺在床上做个活死人。
文宣帝搞不明白,梅园中的韶华同样有点蒙圈。
因为两相有意,又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,桑国与大楚国之间的共开互市,互利互惠,并且还要远嫁秀缘公主的决策以前所未有
的速度,在腊月中旬就已经拟下了双方协议。
之所以未签订正式协议,那还不是因为,大楚国那枚成了精的国玺一直没有下落吗?
不过这事儿同样没拦住合同的正式签订,因为玉王身边现在是人才济济,比如红叶谷的大方道长一听这件事的前因后果,当时
就乐了,“殿下,这根本不是问题啊!”
玉玺都没找到,正式的国书签订不了,这还不是问题,那什么还能称之为问题?
生着一嘴络腮胡须的大方道长呵呵一乐,“殿下,大楚国开国以来,可有签订过此种国书?”
玉王一怔,下意识的回道,“却是无有呢!”
“那不就结了,既然无前例可循,咱这就是头一份啊。
既然没啥具体规定的头一份,谁说了算?
咱自己说了算啊,再者说了,国玺是用在大楚国的国家大事上的,没谁规定外事合约是必须要盖国玺的吧!”
玉王一琢磨也乐了,对啊,他这是形成了固有的思维定式,以前但凡有国家大事,都要盖一份国玺,一来显得郑重,二来感觉
承载着国运的国玺能够起到足够的压制作用。
习惯成自然,不仅是他,连着满朝文武都如此,一听说要答定国书,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国玺。
“道长高议啊!”红叶谷出品,当是不凡,这名声还真不是吹起来的,“惭愧惭愧!”大方道长似模象样的拱了拱手,“食君之禄忠
君之事,当是也。”
这话玉王爱听,吃着我的用着我的花着我的银子,听我差遣,这个没毛病。
“依道长之意,当如何行事?”玉王最近一段时间,因为诸事不合,处处需要仰仗着这帮心腹,也颇有了些礼贤下士的模样,起
码表面现象如此。
大方道长仔细想了一下,这毕竟是代表一个国家尊严的外事印玺,断不可草率,不仅不能草率,而且还不能有可仿性,起码那
些个胡萝卜是仿不来的。
不过,所有这一切,都难不住素有心机的大方道长,于他来说,这都不是事儿,是故慨然道,“殿下,不如找几位臣工前来,大
家一起先商议一下外事玉玺的印刻模式和处理方法,然后再寻人篆刻如何?”
虽然大方道长做这种事得心应手,可他前世虽然没有得到过叶梨歌那般系统的皇储的教育,耳濡目染间,也知道凡事不能急于
求成,更不能一力揽功从而招人忌恨。
有好处大家一起拿,你好我好大家好,这也是帝王平衡术的一种。
玉王当即就差小太监去请人了,这事儿宜早不宜晚,赶想出办法来,赶紧把秀缘公主打发到桑国去。
就说这是个好办法嘛,前段时间,原本狄人已经有大兵压境之势,可韶家人在桑国边境和大楚国边境传出了,桑国要与大楚国
结盟,并将文宣帝之嫡女秀缘公主嫁与桑国老国王和亲的消息,狄人立马就收兵了,一直到如今,不明就理的狄人也没敢冒然
来犯。
这不就是个好兆头吗?
玉王的智囊心腹们没多少时间就齐聚御书房,听得玉王几句简要的说明之后,齐齐伸出大拇指,“妙啊!”